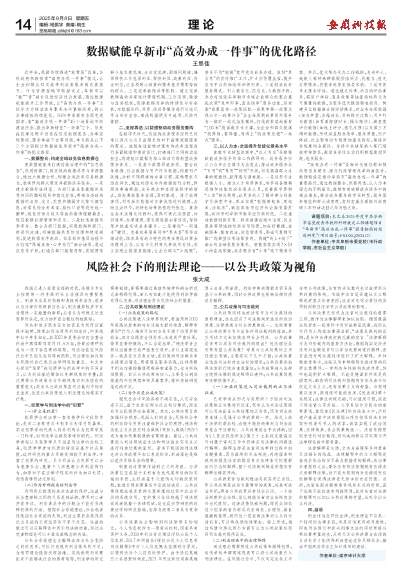发布日期: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理论——以公共政策为视角
文章字数:3238
我国已进入轻罪治理的时代,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刑事立法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姿态,前者认为法律应积极回应社会,刑法谦抑性并不反对增设一定数量的新罪;后者认为积极立法违背罪刑法定,权力的扩张会使权利被限缩。
刑法中诸多罪名设立初衷是为刑罚设置缓冲地带,体现出刑法罪责刑相适应,但实践中似乎并非如此,在2023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中酒驾醉驾案件71.9万起,轻罪治理俨然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难题。刑法功能在风险社会中已经从惩罚转向预防,刑法理论如何契合风险社会已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本文首先探讨“犯罪”在犯罪学与刑法学中的不同含义,认为刑法理论需加以外部视角的考量;其次阐释公共政策作为外部视角对刑法理论的重要意义;最后从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证立出发,论证公共政策进入刑法理论的现实可行性。
一、犯罪学与刑法学中的“犯罪”
(一)什么是犯罪?
犯罪学与刑法学一直有着学科定位的争论,是因二者都将贝卡利亚作为学科的鼻祖。实证犯罪学的代表人物菲利则认为犯罪学是一门科学,而刑法学会被犯罪学所取代。刑法学者则认为犯罪学只不过是刑法学的分析工具,犯罪学学者对犯罪的研究是基于社会角度,这种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相较于刑法学,丰富了犯罪的研究。贝卡利亚认为犯罪可以分为危害社会、危害个人和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果对不在法律中规定的行为加以处罚,则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二)作为外部视角的刑法学
刑罚背后体现的是对法益的保护,法益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学界对二者存在争议。刑法体系中的法概念不能妥当阐释犯罪的内涵。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社会危害性是指社会系统的失效,刑法主要任务是保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不至于失范。法益的概念可以从解释论中展示刑法的功能,而社会危害性理论可以丰富法益概念的内涵。
从社会系统理论去解释法益与社会危险之间的关系,可以补充现有刑法体系的不足,为刑罚理论提供法理基础。实践表明刑法理论并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难题,刑法学的研究需要他律,即需要通过借助其他学科的分析范式来解释犯罪,而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刑法学体系得以完善,刑法理论符合风险社会的需要。
二、公共政策与刑法理论
(一)公共政策的缘起
公共政策进入法学界视野,要追溯到2003年最高法发布的对奸淫幼女罪的批复,解释中提到“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学者主要从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展开,并从主客观是否一致来证立自身立场,在封闭的刑法体系中去推演出理论,再将理论服务实践,这种局限于刑法内部的推理很难具有说服力,也与实践相脱离。而从公共政策来切入,主要是从刑法规范的外在视角审视具体案件,弥补传统研究范式的不足。
(二)为什么是公共政策?
现代社会中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安全感不足,基于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理论,国家应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其次,公共政策旨在加强社会秩序,巩固人们的安全,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的作用更注重维护社会的秩序,刑法的功能主义从报应转为威慑(预防),威慑(预防)成为施加刑事制裁的首要理由。最后,公共政策进入司法领域是立法和司法追求实用主义进行利益均衡的显现。若当下我国的刑法理论对公共政策不加以考虑的话,刑法理论是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需要。
制度设计需要作功利主义的考虑。公共政策往往是基于主权者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实施的手段,主权者基于众意所关切的政策问题,在进行利益衡量后作出政治决定。公共政策体现在追求某种众意实现的过程中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它的意义往往跨越了刑法领域或者说整个法律领域,这也是法学研究的政策法学的研究基础,法律与政策二者具有复杂的关系。
公共政策也会影响到刑法新罪名的创立。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国家具有保护义务,2009年刑法首次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17年两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中对个人信息概念范围进行界定,以便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由于侵犯英雄烈士名誉案件频发,2021年刑法新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刑法中的新增罪名很多是基于公共政策,同时公共政策也影响法律的修改与解释。
三、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
公共政策同样也被法官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理由,这也回应了司法裁判所追求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院常常以公共政策作为作出各种司法裁判的理由,并且用该方式来权衡各种社会利益。公共政策是否可以成为司法裁判的理由?刑法理论是否要考量公共政策?学界对公共政策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政策会造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公共政策会妨碍法官的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进入法律会使得法律的稳定性得以破坏;公共政策的现有法律依据不足。
(一)公共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证成
已有学者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对司法政策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笔者认为其论证思路可以用来论证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因为司法政策本质上是属于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上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院不能拒绝审判与司法政策是合乎法律的。公共政策是合乎法律的,因为《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最高法可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解释法律是法官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因为最终的司法判决、判决理由和裁判依据是法官依据自身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而所作出的解释,整个司法裁判都是依据法官解释法律展开的。
公共政策作为裁判理由具有实质正当性,即公共政策是政治力量博弈的成果,其具有政治共识;再者公共政策具有社会认同。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这涉及着权威问题,即民众相信这个国家的官员都具有正确性、合理性、善良道德的素质,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对公众的行动而言,可以构成排他性理由。综上所述,通过实质与形式两个方面可以为公共政策应用到司法裁判提供证成。
(二)刑法理论中的法律解释
刑法理论需要吸收公共政策来解释犯罪,而法学的外部观察视角可以将公共政策引入刑法理论。在风险社会中,不仅实定法条文中含有公共政策,法官的司法裁判也日益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实践中法官是否遵从文义解释或考虑立法者意图,法官对惩罚必要性的实质性判断往往深受公共政策的影响。
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法官司法裁判的重要工具,被作为法律解释来加以运用。德国最高法院曾在一起案件中肯定盐酸是武器,进而认定行为人构成加重强盗罪。“法理是裁判的总纲,是任何法律决定的沉默的宣言。”法律解释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方法论,德国的实定法并没有对盐酸是否可以作为武器的进行解释,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中进行了扩大解释。牟林翰虐待案中,法院认为牟林翰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一审判决牟林翰构成虐待罪,其中也运用扩大解释。无论是德国案件还是我国案例,都表明司法裁判依据的方法从来不仅仅是文本主义,还有后果主义的考量。当规则难以适用,原则便可能被适用。《民法典》第十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重要原则,体现在《民法典》的其他条文中,泸州遗产继承案中法官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未支持案外利害关系人的诉求,该案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依据原则来进行司法裁判,该判决的背后其实离不开法学理论的外部考量。
法律解释是主体、文本与语境等多种要素互动融合的结晶。法律解释中的文义解释是在追求法治的当下最为被接受的解释,法治要求着规则之治,要求法官依法依据现有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而不是无限制的对法律进行目的解释会使得法律丧失原本的内在价值。当然,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规则失灵的时候,基于法院不能拒绝审判的原则,此时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可以加以公共政策的考量,从而作出公正判决。
四、结语
刑法作为惩罚性法律,刑法理论不应是一个封闭的法律系统,而是应该更具有开放性,即在刑法修订和新兴刑事立法的同时要将公共政策考量进去,只有关注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关系才能使得刑法理论适应风险社会,推动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刑法中诸多罪名设立初衷是为刑罚设置缓冲地带,体现出刑法罪责刑相适应,但实践中似乎并非如此,在2023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中酒驾醉驾案件71.9万起,轻罪治理俨然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难题。刑法功能在风险社会中已经从惩罚转向预防,刑法理论如何契合风险社会已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本文首先探讨“犯罪”在犯罪学与刑法学中的不同含义,认为刑法理论需加以外部视角的考量;其次阐释公共政策作为外部视角对刑法理论的重要意义;最后从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证立出发,论证公共政策进入刑法理论的现实可行性。
一、犯罪学与刑法学中的“犯罪”
(一)什么是犯罪?
犯罪学与刑法学一直有着学科定位的争论,是因二者都将贝卡利亚作为学科的鼻祖。实证犯罪学的代表人物菲利则认为犯罪学是一门科学,而刑法学会被犯罪学所取代。刑法学者则认为犯罪学只不过是刑法学的分析工具,犯罪学学者对犯罪的研究是基于社会角度,这种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相较于刑法学,丰富了犯罪的研究。贝卡利亚认为犯罪可以分为危害社会、危害个人和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果对不在法律中规定的行为加以处罚,则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二)作为外部视角的刑法学
刑罚背后体现的是对法益的保护,法益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学界对二者存在争议。刑法体系中的法概念不能妥当阐释犯罪的内涵。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社会危害性是指社会系统的失效,刑法主要任务是保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不至于失范。法益的概念可以从解释论中展示刑法的功能,而社会危害性理论可以丰富法益概念的内涵。
从社会系统理论去解释法益与社会危险之间的关系,可以补充现有刑法体系的不足,为刑罚理论提供法理基础。实践表明刑法理论并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难题,刑法学的研究需要他律,即需要通过借助其他学科的分析范式来解释犯罪,而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刑法学体系得以完善,刑法理论符合风险社会的需要。
二、公共政策与刑法理论
(一)公共政策的缘起
公共政策进入法学界视野,要追溯到2003年最高法发布的对奸淫幼女罪的批复,解释中提到“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学者主要从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展开,并从主客观是否一致来证立自身立场,在封闭的刑法体系中去推演出理论,再将理论服务实践,这种局限于刑法内部的推理很难具有说服力,也与实践相脱离。而从公共政策来切入,主要是从刑法规范的外在视角审视具体案件,弥补传统研究范式的不足。
(二)为什么是公共政策?
现代社会中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安全感不足,基于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理论,国家应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其次,公共政策旨在加强社会秩序,巩固人们的安全,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的作用更注重维护社会的秩序,刑法的功能主义从报应转为威慑(预防),威慑(预防)成为施加刑事制裁的首要理由。最后,公共政策进入司法领域是立法和司法追求实用主义进行利益均衡的显现。若当下我国的刑法理论对公共政策不加以考虑的话,刑法理论是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需要。
制度设计需要作功利主义的考虑。公共政策往往是基于主权者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实施的手段,主权者基于众意所关切的政策问题,在进行利益衡量后作出政治决定。公共政策体现在追求某种众意实现的过程中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它的意义往往跨越了刑法领域或者说整个法律领域,这也是法学研究的政策法学的研究基础,法律与政策二者具有复杂的关系。
公共政策也会影响到刑法新罪名的创立。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国家具有保护义务,2009年刑法首次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17年两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中对个人信息概念范围进行界定,以便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由于侵犯英雄烈士名誉案件频发,2021年刑法新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刑法中的新增罪名很多是基于公共政策,同时公共政策也影响法律的修改与解释。
三、公共政策与司法裁判
公共政策同样也被法官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理由,这也回应了司法裁判所追求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院常常以公共政策作为作出各种司法裁判的理由,并且用该方式来权衡各种社会利益。公共政策是否可以成为司法裁判的理由?刑法理论是否要考量公共政策?学界对公共政策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政策会造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公共政策会妨碍法官的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进入法律会使得法律的稳定性得以破坏;公共政策的现有法律依据不足。
(一)公共政策进入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证成
已有学者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对司法政策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笔者认为其论证思路可以用来论证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因为司法政策本质上是属于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上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院不能拒绝审判与司法政策是合乎法律的。公共政策是合乎法律的,因为《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最高法可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解释法律是法官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因为最终的司法判决、判决理由和裁判依据是法官依据自身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而所作出的解释,整个司法裁判都是依据法官解释法律展开的。
公共政策作为裁判理由具有实质正当性,即公共政策是政治力量博弈的成果,其具有政治共识;再者公共政策具有社会认同。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这涉及着权威问题,即民众相信这个国家的官员都具有正确性、合理性、善良道德的素质,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对公众的行动而言,可以构成排他性理由。综上所述,通过实质与形式两个方面可以为公共政策应用到司法裁判提供证成。
(二)刑法理论中的法律解释
刑法理论需要吸收公共政策来解释犯罪,而法学的外部观察视角可以将公共政策引入刑法理论。在风险社会中,不仅实定法条文中含有公共政策,法官的司法裁判也日益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实践中法官是否遵从文义解释或考虑立法者意图,法官对惩罚必要性的实质性判断往往深受公共政策的影响。
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法官司法裁判的重要工具,被作为法律解释来加以运用。德国最高法院曾在一起案件中肯定盐酸是武器,进而认定行为人构成加重强盗罪。“法理是裁判的总纲,是任何法律决定的沉默的宣言。”法律解释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方法论,德国的实定法并没有对盐酸是否可以作为武器的进行解释,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中进行了扩大解释。牟林翰虐待案中,法院认为牟林翰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一审判决牟林翰构成虐待罪,其中也运用扩大解释。无论是德国案件还是我国案例,都表明司法裁判依据的方法从来不仅仅是文本主义,还有后果主义的考量。当规则难以适用,原则便可能被适用。《民法典》第十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重要原则,体现在《民法典》的其他条文中,泸州遗产继承案中法官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未支持案外利害关系人的诉求,该案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依据原则来进行司法裁判,该判决的背后其实离不开法学理论的外部考量。
法律解释是主体、文本与语境等多种要素互动融合的结晶。法律解释中的文义解释是在追求法治的当下最为被接受的解释,法治要求着规则之治,要求法官依法依据现有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而不是无限制的对法律进行目的解释会使得法律丧失原本的内在价值。当然,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规则失灵的时候,基于法院不能拒绝审判的原则,此时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可以加以公共政策的考量,从而作出公正判决。
四、结语
刑法作为惩罚性法律,刑法理论不应是一个封闭的法律系统,而是应该更具有开放性,即在刑法修订和新兴刑事立法的同时要将公共政策考量进去,只有关注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关系才能使得刑法理论适应风险社会,推动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