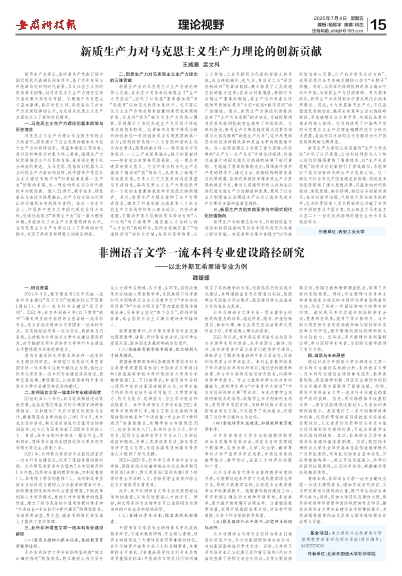发布日期: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贡献
文章字数:1997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征程中,基于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宝库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应时代之问,系统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入了新的时代精华。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与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持续进步。其基本框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核心要素,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形态的更迭。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力革命的剖析,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丰富,这一理论始终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向前发展。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绿色革命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重构。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系统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入了崭新的时代精华,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
二、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三维贡献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贡献,首先在于其革命性地提出了“生产力质态论”,实现了从传统“要素叠加观”向“系统质”认知范式的历史性跃升。它不再仅仅关注生产力构成要素数量的累积或规模的扩张,而是将“质态”确立为生产力的核心属性,深刻揭示了当代先进生产力区别于传统形态的根本特质。这种新质态集中体现为鲜明的创新性—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刻的绿色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内在要求;高度的融合性——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强大的高韧性——够有效应对复杂风险挑战。这一理论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它为科学分析当代生产力提供了精准的“质”的标尺,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发展观,引导人们关注发展的内在质量与可持续性,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升到一个更加注重整体效能和系统优化的新境界。其次,新质生产力理论重构了生产力要素体系,确立了科技创新与高素质人才在当代生产力系统中的核心驱动地位。在劳动者维度,它推动中国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向以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核心的“人才红利”战略转变,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创造性劳动”的巨大价值;在劳动资料维度,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智能工具系统,成为继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之后“劳动资料跃升”的最新载体,极大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边界;在劳动对象维度,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崛起,将生产活动对象从传统物质领域拓展至“太空+深海+数字空间”的广阔疆域。最后,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性地发展了“生产关系适配”的方法论,为破除阻碍其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指明了实践路径。它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涉及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将经典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创造性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语境下进行重构。它超越了简单线性决定论,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主动、前瞻性的制度变革与政策调整,能够有效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上层建筑积极主动地适应并促进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主动调适生产关系以适应先进生产力要求方面的显著优越性。
三、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指向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其深刻的实践指向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驱动价值。其发展要求集中体现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以产业升级为主攻方向”。这要求我们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同时,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质生产力扫清障碍。更为根本的是,新质生产力深刻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塑造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抉择,更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核心密码。它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精髓的坚守与时代化发展,是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发展课题的光辉典范。
新质生产力理论以其深邃的“生产力质态论”升华了认识维度,以对科技创新与人才核心地位的强调重构了要素体系,以“生产关系适配”的方法论创新指引了实践路径,系统回应了数字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之问。这一理论不仅为当代中国突破发展难题、构筑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其蕴含的对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融合协调、韧性安全的深刻洞见,在应对数字治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也为世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澎湃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力。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与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持续进步。其基本框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核心要素,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形态的更迭。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力革命的剖析,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丰富,这一理论始终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向前发展。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绿色革命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重构。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系统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入了崭新的时代精华,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
二、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三维贡献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贡献,首先在于其革命性地提出了“生产力质态论”,实现了从传统“要素叠加观”向“系统质”认知范式的历史性跃升。它不再仅仅关注生产力构成要素数量的累积或规模的扩张,而是将“质态”确立为生产力的核心属性,深刻揭示了当代先进生产力区别于传统形态的根本特质。这种新质态集中体现为鲜明的创新性—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刻的绿色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内在要求;高度的融合性——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强大的高韧性——够有效应对复杂风险挑战。这一理论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它为科学分析当代生产力提供了精准的“质”的标尺,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发展观,引导人们关注发展的内在质量与可持续性,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升到一个更加注重整体效能和系统优化的新境界。其次,新质生产力理论重构了生产力要素体系,确立了科技创新与高素质人才在当代生产力系统中的核心驱动地位。在劳动者维度,它推动中国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向以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核心的“人才红利”战略转变,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创造性劳动”的巨大价值;在劳动资料维度,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智能工具系统,成为继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之后“劳动资料跃升”的最新载体,极大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边界;在劳动对象维度,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崛起,将生产活动对象从传统物质领域拓展至“太空+深海+数字空间”的广阔疆域。最后,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性地发展了“生产关系适配”的方法论,为破除阻碍其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指明了实践路径。它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涉及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将经典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创造性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语境下进行重构。它超越了简单线性决定论,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主动、前瞻性的制度变革与政策调整,能够有效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上层建筑积极主动地适应并促进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主动调适生产关系以适应先进生产力要求方面的显著优越性。
三、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指向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其深刻的实践指向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驱动价值。其发展要求集中体现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以产业升级为主攻方向”。这要求我们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同时,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质生产力扫清障碍。更为根本的是,新质生产力深刻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塑造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抉择,更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核心密码。它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精髓的坚守与时代化发展,是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发展课题的光辉典范。
新质生产力理论以其深邃的“生产力质态论”升华了认识维度,以对科技创新与人才核心地位的强调重构了要素体系,以“生产关系适配”的方法论创新指引了实践路径,系统回应了数字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之问。这一理论不仅为当代中国突破发展难题、构筑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其蕴含的对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融合协调、韧性安全的深刻洞见,在应对数字治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也为世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澎湃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力。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