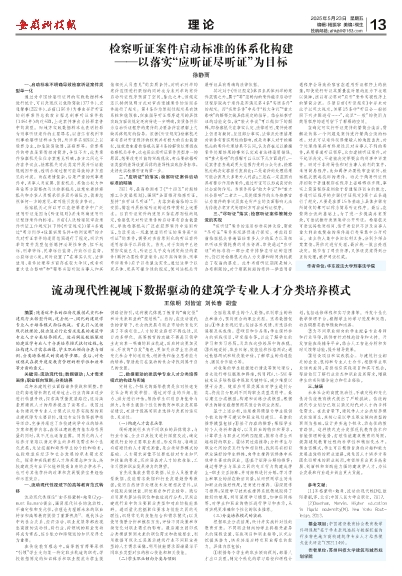发布日期:
检察听证案件启动标准的体系化构建 ——以落实“应听证尽听证”为目标
文章字数:2388
一、启动标准不明确导致检察听证案件类型单一化
通过对中国检察听证网的实践数据样本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仅以危险驾驶(377件)、交通肇事(222件)、盗窃(186件)为事由召开听证的刑事案件总数就占据总刑事听证案件数(1464件)的近60%,上述案件事由为轻罪案件中的典型。而地方实践数据样本也表明轻罪为刑事听证案件的主要罪名,以浙江省杭州市刑事检察听证样本为例,所涉罪名90%以上以轻罪为主,如危险驾驶罪、盗窃罪等。轻罪案件的特点是案情相对简单,争议不大,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往往办案意见明确,各方之间也不存在争议点,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展开听证能规避因开放、透明办案过程可能导致的多方意见的冲突。而在案情复杂、后果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及家属、侦查机关、其他公权力和舆论等方面都在关注检察机关,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需承担多层外部压力,倘若忽视任何一方的意见,都可能引发较多争议。
检察机关之所以可以在轻罪案件中广泛适用听证是因为《听证规则》并未明确适用听证程序案件的标准。当前《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下称《听证规定》)第4条通过“明示列举+设置实质条件+特例说明”的方式对听证案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明示列举的案件类型包括羁押必要性审查、拟不起诉、刑事申诉、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6类,同时设置了“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和“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实质条件,对明示列举的案件范围进行限缩的同时也为未列举的案件启动听证程序预留了空间,除此之外,该规定还以特例说明方式对审查逮捕案件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规定。第4条作为原则性规定具有体系性和统领性,但在指导听证程序适用的具体实践方面该规定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实质条件作为启动听证程序的案件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上欠缺具体规定的指导。依据《听证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启动听证程序的权利并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第4条的解读权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这也是出现听证案件类型单一的原因,想要改变目前的实践现状,有必要依据听证类型的差异设置具体的差异性实践指导标准,走好走实检察听证的第一步。
二、“应听证”的落实:检察听证案件启动标准的明确
2021年,最高检颁布了《“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强调“全面推开检察听证,坚持‘应听证尽听证’”。为落实最高检的工作安排,需在开展检察听证的过程中贯彻上述要求。目前听证案件的适用只存在原则性的规定,检察机关对听证案件的启动享有自由裁量权,导致检察机关广泛在轻罪案件中适用听证,为改变这一现象使适用听证的案件是“应听证”的案件,需要对当前原则化的听证案件适用标准予以具体化。首先,对于实践中已经贯彻实施已久,听证已几乎成为固定做法的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应予以类型法定化,通过法律予以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开展听证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听证规定》第四条具体列举的案件范围之外,属于“等”范畴内的案件能否启动听证程序取决于案件是否满足第4条“实质条件”的规定。而“实质条件”中关于“较大争议”“重大影响”的解释欠缺具体规定的指导。结合检察听证的功能定位,就“较大争议”可以做如下的解释,即检察机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上仍旧有疑问,且这部分事实、法律及处理结果对案件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或是当事人对于检察机关的案件处理结果不认同,认为存在足以推翻案件处理结果的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错误。而“重大影响”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案件在当地或更大范围内受到公众关注,检察机关的决定容易引发舆论;二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会波及众多案外人利益;三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警示作用的案件,通过听证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宣传作用。当案件具备“较大争议”和“重大社会影响”二者之一,且处理案件的主办检察官认为案件的争议及舆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无法为传统办案方式处理时方可启动听证程序。
三、“尽听证”落实:检察听证案件繁简分流的实现
“应听证”案件的适用标准具体化后,需就“尽听证”案件实现路径进行探究。考虑到目前检察机关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以及组织听证所需耗费的司法资源,即使通过“应听证”的标准将一部分案件排除在听证的范围外,仍旧对检察机关的人力支撑和时间消耗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当前听证期限是纳入办案期限的,对于期限较短的案件一律适用普通程序会导致检察官在适用听证程序上的犹豫,即使进行听证其质量在时限的压力下也难以保障,所以有必要对“应听”案件实现程序上的繁简分流。尽管目前《听证规定》中并未对此予以明文规定,但第15条中“听证会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这里“一般”的使用为简易程序的适用留下了解释的空间。
在确定可实行听证案件的繁简分流后,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的标准。对此可从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出发,对于处理结果具有终局性且对当事人不利的案件,采用普通听证程序,比如逮捕听证案件,对不起诉决定、不逮捕决定等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而对于非终局性和对当事人有利的案件,采用简易程序,比如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而关于简易听证程序相较于普通程序在程序上省略哪些步骤,事实上简易程序是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的概念,普通听证程序的步骤《听证规定》第十五条进行了规定,只要是在第15条基础上具体步骤有所简化的都可以称为简易听证程序。最后,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办案质效,可尝试推行类案集中公开听证。检察机关可尝试将性质相同、情节类似但不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或复杂的案件进行类案集中公开听证。由主持人集中告知权利义务,分别介绍各案案情,再依次进行处理,最后统一做出处理决定。既节省了司法资源,又保证类案得到公正的处理,维护司法权威。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通过对中国检察听证网的实践数据样本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仅以危险驾驶(377件)、交通肇事(222件)、盗窃(186件)为事由召开听证的刑事案件总数就占据总刑事听证案件数(1464件)的近60%,上述案件事由为轻罪案件中的典型。而地方实践数据样本也表明轻罪为刑事听证案件的主要罪名,以浙江省杭州市刑事检察听证样本为例,所涉罪名90%以上以轻罪为主,如危险驾驶罪、盗窃罪等。轻罪案件的特点是案情相对简单,争议不大,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往往办案意见明确,各方之间也不存在争议点,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展开听证能规避因开放、透明办案过程可能导致的多方意见的冲突。而在案情复杂、后果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及家属、侦查机关、其他公权力和舆论等方面都在关注检察机关,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需承担多层外部压力,倘若忽视任何一方的意见,都可能引发较多争议。
检察机关之所以可以在轻罪案件中广泛适用听证是因为《听证规则》并未明确适用听证程序案件的标准。当前《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下称《听证规定》)第4条通过“明示列举+设置实质条件+特例说明”的方式对听证案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明示列举的案件类型包括羁押必要性审查、拟不起诉、刑事申诉、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6类,同时设置了“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和“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实质条件,对明示列举的案件范围进行限缩的同时也为未列举的案件启动听证程序预留了空间,除此之外,该规定还以特例说明方式对审查逮捕案件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规定。第4条作为原则性规定具有体系性和统领性,但在指导听证程序适用的具体实践方面该规定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实质条件作为启动听证程序的案件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上欠缺具体规定的指导。依据《听证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启动听证程序的权利并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第4条的解读权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这也是出现听证案件类型单一的原因,想要改变目前的实践现状,有必要依据听证类型的差异设置具体的差异性实践指导标准,走好走实检察听证的第一步。
二、“应听证”的落实:检察听证案件启动标准的明确
2021年,最高检颁布了《“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强调“全面推开检察听证,坚持‘应听证尽听证’”。为落实最高检的工作安排,需在开展检察听证的过程中贯彻上述要求。目前听证案件的适用只存在原则性的规定,检察机关对听证案件的启动享有自由裁量权,导致检察机关广泛在轻罪案件中适用听证,为改变这一现象使适用听证的案件是“应听证”的案件,需要对当前原则化的听证案件适用标准予以具体化。首先,对于实践中已经贯彻实施已久,听证已几乎成为固定做法的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应予以类型法定化,通过法律予以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开展听证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听证规定》第四条具体列举的案件范围之外,属于“等”范畴内的案件能否启动听证程序取决于案件是否满足第4条“实质条件”的规定。而“实质条件”中关于“较大争议”“重大影响”的解释欠缺具体规定的指导。结合检察听证的功能定位,就“较大争议”可以做如下的解释,即检察机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上仍旧有疑问,且这部分事实、法律及处理结果对案件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或是当事人对于检察机关的案件处理结果不认同,认为存在足以推翻案件处理结果的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错误。而“重大影响”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案件在当地或更大范围内受到公众关注,检察机关的决定容易引发舆论;二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会波及众多案外人利益;三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警示作用的案件,通过听证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宣传作用。当案件具备“较大争议”和“重大社会影响”二者之一,且处理案件的主办检察官认为案件的争议及舆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无法为传统办案方式处理时方可启动听证程序。
三、“尽听证”落实:检察听证案件繁简分流的实现
“应听证”案件的适用标准具体化后,需就“尽听证”案件实现路径进行探究。考虑到目前检察机关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以及组织听证所需耗费的司法资源,即使通过“应听证”的标准将一部分案件排除在听证的范围外,仍旧对检察机关的人力支撑和时间消耗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当前听证期限是纳入办案期限的,对于期限较短的案件一律适用普通程序会导致检察官在适用听证程序上的犹豫,即使进行听证其质量在时限的压力下也难以保障,所以有必要对“应听”案件实现程序上的繁简分流。尽管目前《听证规定》中并未对此予以明文规定,但第15条中“听证会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这里“一般”的使用为简易程序的适用留下了解释的空间。
在确定可实行听证案件的繁简分流后,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的标准。对此可从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出发,对于处理结果具有终局性且对当事人不利的案件,采用普通听证程序,比如逮捕听证案件,对不起诉决定、不逮捕决定等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而对于非终局性和对当事人有利的案件,采用简易程序,比如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而关于简易听证程序相较于普通程序在程序上省略哪些步骤,事实上简易程序是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的概念,普通听证程序的步骤《听证规定》第十五条进行了规定,只要是在第15条基础上具体步骤有所简化的都可以称为简易听证程序。最后,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办案质效,可尝试推行类案集中公开听证。检察机关可尝试将性质相同、情节类似但不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或复杂的案件进行类案集中公开听证。由主持人集中告知权利义务,分别介绍各案案情,再依次进行处理,最后统一做出处理决定。既节省了司法资源,又保证类案得到公正的处理,维护司法权威。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